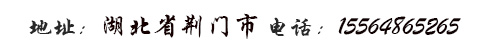我怀了反派的崽,而这个反派是大名鼎鼎的九
|
我怀了反派的崽,而这个反派……是大名鼎鼎的九千岁? 我摸着刚穿越过来的这具身体,一时间竟不知道到底是谁天赋异禀…… 1、 没什么是比一个铁丁克穿越成了一个足月的孕妇更惨的事情了吧? 跳过了造孩子的快乐时候,一步跨到了生孩子的悲惨雨夜。 说来也怪我,本来可能没这么快生的,我这不是刚穿越过来人生地不熟嘛,旁边屋子正好有动静,就去扒门缝偷听。 结果听到一个青年男人在给人汇报,“九千岁,产婆说,雾姑娘落水受惊还未醒,但算算日子,生产就这几日了。” 雾姑娘?我?九千岁?太监? 另一个稳重老成的人说,“九千岁,这孩子您看是留在京中,还是送回潭州呢?” 这时,一个冷冰冰的声音,淡淡说了一句,“儿子就留京中,女儿送回潭州。” 老人开心的笑了,说,“是的是的,是小公子的话就以您义子的名义留在身边好好培养,小姑娘当送回潭州陪伴老夫人,老夫人一定疼爱孙女。” 老人声音说到后面竟有些哽咽。 青年男人也笑了,对老人说,“父亲,您怎哭了啊?” 老人情绪激动,说,“我是高兴,九千岁这些年在宫……实在是不容易啊!老主人要是在天之灵知道九千岁有后了,我在九泉之下也有脸见老主人了啊!” 我的崽是九千岁的?九千岁不是应该……嗯……少点什么关键零件吗? 那个九千岁安抚老人,说,“须伯,您不用过于感怀,当心身体。” 须伯对九千岁的关怀受宠若惊,连声称是,随即问,“九千岁,那雾姑娘,当如何?” 叭叭了半天,终于说到我了! 九千岁没有半分犹豫,声音轻得有些随意,“去母留子。” 2、 去母留子? 窗外一道惊雷劈下,气氛被渲染得我不怕都不行。 我一口气差点没提起来,不会吧不会吧,孕妇一日体验卡吗? 不行不行,我赶紧回了自己的房间,无助的环顾一圈,好像也没什么要收拾的,这得跑路,这必须跑路! 去母留子啊!!! 门口的婢女看我一脸慌张,立刻过来问我怎么了。 我也不知道这个婢女可信不可信,所以并不打算和她说什么,转身就准备出逃。 却感觉腿间一股热流,肚子开始疼了起来…… 完了……这难道是惊吓过度动了胎气? 婢女也发现了,我还来不及说话,她就惊乍乍的冲了出去,边跑边喊,“雾姑娘羊水破了——雾姑娘羊水破了——!” 完了…… 接下来的一整夜,我经历了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。 可哪怕就是生孩子的时候,我痛得几乎昏厥,都在一边用力一边想,去母留子,怎么办啊! 清晨的阳光和小孩的啼哭一起到来,可产婆并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便宜崽给我看,而是直接抱了出去,远远听到产婆兴奋的喊着,“是小公子,是小公子!” 力竭的我躺在床榻上,脑子还在进行最后的思考,垂死挣扎。 很快,须伯和一个年轻人进来了,这应该就是他儿子吧。 须伯看着我,假惺惺的说,“雾姑娘辛苦了。” 我是人之将死,其言也刚,白了他一眼,夹枪带棒的说,“辛苦你了才对,我刚生完孩子腿都没力气合上就来杀我了。” 须伯显然是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,停了一会,对他儿子说,“既然雾姑娘如此通透,你让产婆把小公子抱进来,送雾姑娘一程,也是感怀雾姑娘怀胎十月一朝产子之恩。” 产婆很快抱着我儿子进来了,他不像其他新生儿那么干瘪,皮肤特别白,虽然还有些没有脱水的褶子,但一点也盖不住他的好看。 一瞬间,丁克多年的我竟有点母爱泛滥了,原来有孩子是这样的感觉…… 产婆抱着我儿子时,他哭得那叫一个声音洪亮,真怕他把嗓子哭坏了。 产婆看须伯儿子手把着剑的这架势,估计也是知道点什么,把我扶坐起来,将孩子放我怀里,说,“快抱抱你儿子,快抱抱他。” 我感恩的看了一眼产婆,谁知道小家伙到我怀里一下就不哭了,眨巴着眼睛看着我。 这孩子大眼睛像极了我,我是说本来的现代的那个我,事实上我都不知道这个雾姑娘到底长啥样,他仿佛有些累了,嘴唇一蠕一蠕的,可爱极了。 片刻,须伯儿子示意产婆抱走小家伙,产婆怜惜的看了我一眼,伸手来抱孩子。 我没有为难产婆,把昏昏欲睡的孩子递给了她,谁知我刚一脱手,小家伙就开始大声啼哭,一声高过一声,完全不像正常孩子的哭声,像是声嘶力竭的嚎叫。 产婆看着须伯,说,“老管家,这是孩子舍不得母亲啊!” 须伯不置可否,产婆壮着胆子又把孩子放回了我怀里,孩子瞬间就不哭了,眨巴着眼睛看着我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,竟觉得他有些得意。 如此反复几次,都是孩子一离开我怀里就不要命的哭,一挨着我就老实乖巧可爱。 须伯看到这一幕,估计是心疼他口中的小公子吧,终于开口了,对他儿子说,“你去回禀主子此情景,且让孩子再亲昵他母亲一日,明日我们再来。” 须伯儿子看着自己的父亲,说,“可是……” 须伯摆了摆手,打断了他的话,说,“服侍主子几十年了,这点主我还是可以做的。” 说完须伯带着他儿子离开了。 知道须伯走远,我看着怀里乖巧的儿子,心念一转,想到了什么,随即让产婆过来抱他。 果然,孩子没有再哭闹,看了我两眼,估计是刚才闹累了,没两分钟就睡着了。 我看着酣睡的小肉球,心想:这孩子,是在救我啊。 3、 我不能浪费小家伙给我争取的一天时间! 房门口并没有守卫,我可以去院子逛逛,但是他们明天是要来杀我的,不可能让我跑了,再说,凭我现在的体力,别说守卫了,产婆都能把我按倒。 我老实的坐在院中的凳子上头脑风暴。 九千岁,太监,莫名其妙有了孩子,难道是干净之前搞的? 十个月就能当上九千岁,太监升职记啊? 这古代的太监都是从小孩开始的,那这九千岁十有八九就是假太监。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是他的孩子,杀我是为了灭口。 那我为了活下来,要么表示我永不会告诉别人,要么就是我还有更大的价值。 永不告诉别人这事,我就算说我能做到,他也不会相信啊。 那我只有提供价值了…… 对于一个太监,我提供什么价值最好呢? 断肢重生? 脑补了一下,咦惹…… 且不说他是不是断肢,我还是不要试图去攻克现代医学都没办法搞定的难题了。 现代,现代,现代,现代能有啥能给一个古代的太监提供价值的啊? 就在我绞尽脑汁一筹莫展的时候,产婆抱着孩子过来了,我看着产婆,试图打开话茬,笑嘻嘻的问她“婆婆,你早上为什么帮我啊?” 产婆坐在我旁边,说,“你啊,你还笑得出来,他们要你命啊你知道不?” 我心想有戏,这产婆好像知道点什么,就问,“你怎么知道啊?” 产婆叹了一口气,说,“你这种我看多了,你啊,肯定是哪家大户人家在外面养的小娘子,以为有了孩子就可以进主人家了,这种主人家更留不得你的,你知道吗?” 我还以为产婆知道点什么,搞半天全是脑补啊,我顺着她的思路和她编排了下去。 不一会,我一个小三上位不成反要被杀的悲惨形象也就立住了。 产婆感叹道,“哎,乱世啊,人命如草芥啊!” 我看话都铺垫到这里来了,就问产婆,“婆婆,你知道九千岁是谁吗?” 我话刚说完,产婆跟中邪了一样,赶紧腾了一只手来捂我的嘴,说,“噤声!” 这么恐怖? 产婆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,声音极低说,“你好歹也是个京都名角,寄语楼的头牌歌姬,见识过达官贵人的,怎么这般不小心,随口议论九千岁呢?” 我且不管什么名角歌姬寄语楼,也跟着话茬小声说,“为啥不能说他?” 产婆声音更低了,说,“九千岁为什么叫九千岁,那是就比万岁少了一千岁啊!当今万岁软弱多病,京中孩童都知道,九千岁要是有根,怕是万岁也坐不住了!” 这么狂?这不是究极奸佞吗? 我看着产婆,更更更小声说,“可为什么这个院子人都没有,我们还要这么小声说话啊?” 产婆又挖了我一眼,更更更更小声说,“传说九千岁眼线遍布天下,听天下之声,晓天下之事,杀天下不臣之人,诛天下不服之众。” 噢,情报杀手机构呗,真是朝廷要想发展好,恐怖机关少不了啊。 想到这里,我突然看到了一线生机,大喊“我想到办法了!” 产婆被我吓得整个人一抖,差点把小家伙扔地上,扶着胸口说,“哎哟,雾姑娘你这是咋了你,你吓死老太婆我了!” 我看向产婆,说,“婆婆,我待会给你开个单子,你出去帮我买点东西,我要救命用。” 产婆狐疑的看着我,不做动作,我说,“别担心,肯定肯定不会连累你的,你到时候看单子,要是有什么刀枪棍棒啥的不妥的,你就直接去找那个老头告我去,行吧?” 产婆继续狐疑的看着我,我是一个枣子一个巴掌,又说,“也行,反正我明早他们就要来杀我了,照你说的,人命如草芥,你说他们可不可能就是连你也一起杀了,这样永绝后患,反正你也把事情猜出来了,杀一个也是杀,杀两个那还少洗一次刀,是吧?” 产婆眼神里终于浮出了恐惧,颤颤巍巍的说,“这,这不合我们这行的规矩……” 我直视她的眼睛,一字一句的说,“你想想,这城里,就没有突然失踪的产婆么?” 产婆彻底被我吓住了,我再点上一句,“我死了,你也要死,我活着,你才可能活着!” 产婆被我吓出一脑门子汗,转身就去屋里给我找纸笔去了。 呼,但愿我这法子有用。 4、 产婆很快买回来了我要的东西,好在这九千岁只要我命,不要我的钱。经过产婆提醒,我才知道我手上的这个手镯就价值不菲,赶紧给她拿去买东西。 我估计手镯变卖了还有剩,但是产婆不提,我也懒得和她掰扯。 此时,桌面上摆着我让产婆买回来的蜂蜡,油,松香,淀粉,还有矿石做的粗糙颜料,以及这个时代的一些化妆品。 说是化妆品,我翻看了一下,也就是眉笔,散粉,腮红,口红这几样,多的也没有了。 够了够了。 产婆发愁的看着我这一桌子东西,说,“雾姑娘啊,你本身就很美了,你是想打扮得更好看去求情吗?且不知主人家会不会心软,你可能都没办法见着主人家啊!” 这产婆脑补能力是真的一流,根本不用我费脑筋,她就自己把自己骗好了。 我看着面前这个铜镜歪歪扭扭的,便让婢女去打了一盆水来,免得太过失真。 产婆看我这一系列操作直摇头。 我仔细端详了产婆的样貌后,忽悠她去休息,产婆将信将疑的抱着孩子离开了屋子,我便开始了我美妆博主的自救之路。 做肤蜡,改面部线条,做皱纹,勾阴影…… 几个小时之后,我总算是把自己大致画成了产婆的模样。 但由于材料质量不行,细看破绽百出,而且这肤蜡估计坚持不了多久,我也来不及太注意着装,找了个灰扑扑的外衣套上,再裹了个头巾遮住头发,勉强模仿着产婆的姿势,就往门口出发。 儿子,对不住了,你留在这里不会死,可你妈会死。 你妈我就先行一步了,咱俩有缘再见。 一路畅通的走到门口,侍卫见我是产婆,端详了几眼,说,“你今天不是已经出去过了吗?” 我故意哑着嗓子说,“我这受寒了,我得去找医……郎中看病,不然传染给小公子就麻烦了……” 侍卫将信将疑的看了我一眼,抬手放我出去了。 这条街好长,我也不敢回头,侍卫肯定是看着我的,我就这样勾着背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前再走。 拐过街角,确认侍卫是看不到我了,我这才松了一口气,赶紧找了个台阶坐下。 天已见黑,路上的人也少了。 身体有些受不了了,这毕竟才生孩子,这要放现代,你跟我说前一天晚上通宵生孩子,第二天还能走,我都觉得是超人。 没想到人真的是逼出来的。 我掂了掂怀里的首饰和剩余的化妆材料,拦了个路人,问最近的客栈在哪里。 好在真不远,再远我真走不动了,生产完月子都不坐,半夜在这里吹风,我好怕自己会得妇科病啊…… 这件客栈挺大的,我掏出了一件首饰,问老板,“我没现钱,这个,能住多久?” 老板眼力一阵精光,随即马上按了下去,换上了一脸嫌弃的表情,说,“老太,你这玉佩的成色不行啊,给你抵3天房钱吧!”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,说,“一个月。” 老板连忙说,“不行不行,这样吧,我看你年纪大了,最多给您10天。” 虽然老板嘴上这么说,但是眼睛却掉在了这个玉佩上。 我看不懂玉,但我看得懂人的贪婪。 我啪一拍桌子,“一个半月,不让住我走了,玉佩给我。” 老板见我伸手来拿玉佩,想也不想马上就揣进了自己的怀里,说,“行行行,一个半月,您说您明明懂,还装什么不懂呢真是。” 我此刻都快站不住了,冷汗直冒,不过倒也符合我老太的模样,颤颤巍巍的,我跟着老板上了楼。 这客栈房间不大,中间一张餐桌,右边一张床,左边就是浴盆和上厕所的桶。 我让老板随便给我炒俩个菜再打点热水洗澡,这才知道,在客栈,每天住宿是会送家常菜的,当然,那些贵的菜是必须单独算钱的。 还挺人性化。 草草卸了妆,我也管不了月子期间能不能泡澡这件事,把整个人泡在浴盆里,温暖的水流包裹全身,忍不住颤抖的身体总算是平复了下来。 身上隐隐还有血腥味,我看着自己穿越而来的身体,白净,纤细,即便是生了孩子,除了肚子上的肉略有松弛,其他地方和未婚少女没有什么区别。 这大概就是真的天生丽质吧…… 5、 明天一早,他们就会发现我跑了,肯定会到处搜捕我。 我这情况,也没办法走太远,他们也会知道我化妆成了产婆的模样,只能明早再化妆成另一个模样,只要第一波严查躲过了,后面的肯定会松泛一些,等我这边在客栈坐完月子,再谋后路。 打定主意后,我起身收拾一下准备去催催老板送晚饭来。 我已经要饿得低血糖了。 费劲的穿好里衣,还在琢磨外衣怎么穿,小二就来敲门了,我连忙让他进来。 门开了,确实是端着餐盘的小二,只不过后面还跟着两个人。 一个是须伯,另一个是他儿子。 我吓得连退几步,踢翻了凳子跌坐在地上,怎么,怎么这么快…… 须伯脸上一片温和,他早上要杀我的那会也是一片温和! 他让小二把饭菜放桌上,然后进来,示意他儿子把门关上,说,“雾姑娘,好本事啊!” 我强装镇定,说,“你们,你们怎么知道我跑了的?” 须伯笑着说,“雾姑娘怕不是落水给溺傻了,你的一举一动,都在九千岁眼里,之前你不都已经认清事实了吗?” 我认清你个屁,臭老头,装你个鬼。 须伯指了指桌上的饭菜,说,“我来时知雾姑娘正在洗浴,没有打扰,吩咐厨房弄了几个这边出色的菜,雾姑娘尝尝。” 我壮着胆子,语气不佳的说,“干嘛,吃完好上路是吧?” 须伯笑盈盈的说,“不知雾姑娘从何习得这易容之术,我朝易容之术早已绝传,虽九千岁下令去母留子,但小老儿觉得,作为此术传承,雾姑娘的性命,可再做商榷。” 行吧,垄断性技术人才呗。 知道自己暂时是死不了了,我也是松了一口气,倒也不客气,愣是吃到打嗝了才放下筷子,须伯和他儿子就在边上看着我,也不催我,看得我瘆得慌。 吃完,须伯做了一个请的姿势,我让他儿子带上我的化妆用品,随他们父子离开。 哎,逃了,但没完全逃。 路过掌柜柜台时,我想起了我的玉佩,上去一拍桌子,说,“玉佩还我!我一天都没住完!” 掌柜的看了眼我,看了眼须伯,居然没有问我是谁,也没有反抗,直接把玉佩毕恭毕敬还给了我。 我看了眼旁边的须伯,看来真的是九千岁只手遮天啊。 我坐的马车是全封闭的,只有几个不透光的气孔,丝毫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。 古代的车轮就只有轮没有胎,颠得我七荤八素的,胃里的食物翻江倒海,难受得不行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须伯打开了马车的门,吩咐人摆好小梯子,扶我下了车。 这里是一处很大的宅院,须伯也没像电影一样蒙住我的头,而是直接带着我往里屋走去。我身体毕竟还是很虚弱,走得很慢,须伯也不催我,随我慢行。 到地方后,须伯嘱咐了下人几句,让我在这里等着,就离开了屋子。 接下来,就是漫长的等待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都困得不行了,门开了,须伯回来了,他前面站着的,是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,穿着一身黑衣,五官棱角分明,剑眉星目,特别好看。 须伯躬身说,“九千岁,雾姑娘带回来了。” 我瞳孔都放大了,这就是九千岁?喔!太监颜值天花板了啊! 九千岁走上前,在主位坐下,看了我两眼,才开口说话,“你可还恨我?” 我被这个问题问得一头雾水,看了看九千岁,看了看须伯,不知道怎么回答。 九千岁见我不回答,又说,“怎以前不知道你还会易容此等绝技?” 我还没来得及说啥,他又说,“演示给我看看,”随即吩咐,“须齐。” 由不得我分说,须伯的儿子须齐就把我的那些化妆材料铺陈在了我面前,人也坐了过来,对我说,“你把我易容成九千岁的模样。” 我看了看须齐,又看了看九千岁,摇头说,“画不了。” 九千岁身子略歪靠在椅子上,饶有兴趣的说,“为何?” 我伸手量了量须齐脸的大小,看得出他很抗拒,但是还是忍住没反抗。我又保持着手的姿势,走到九千岁面前,想去量他脸的大小。 须伯见我这样,大喊,“贱婢敢尔?” 我吓得一抖,九千岁伸手示意,说,“无妨。” 比量之后,我说,“你看,须齐的脸比你的脸足足大这么多,我化妆呢主要是靠雕塑肤蜡,来增加面部的肌肉和纹理,达到相似,那脸本身就比你大这么多,我只能做加法不能做减法啊,我总不能把须齐脸上的肉割下来把。” 须齐闻言,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。 九千岁好似笑了,但感觉又并没笑,只说,“有趣,有理。” 须伯反应了过来,说,“九千岁,路家旁系有一子弟,脸型与您颇为相似。” 九千岁点头,须伯就准备退下去找人,九千岁看了我一眼,说,“明日吧,今日太晚了。” 我看着和我近在咫尺的九千岁,听到他说今天就这样收工了,脑子一直绷着的一根弦瞬间松了,终于体力不支,滑坐在地上。 九千岁站了起来,居高临下的看着瘫坐在地的我,说,“你可还恨我?” 我已无力思考,更不知道怎么回答,极限透支的体力和脑力让我觉得要是此刻就这么死了,那也算是解脱。 九千岁躬身,毫不费力的抱起了我,他的手臂过于有力,我从没在这么稳当的怀抱里沉浸过,紧绷的神经有些些许放松。 不自觉的,我喊他,“九千岁……” 他没看我,只是说,“累了就睡吧。” 6、 我不知道这个雾姑娘和这九千岁到底是什么关系。 为什么昨晚上还是一句冷冰冰的去母留子,今晚就能这么温柔的抱我回屋? 他到底是不是太监? …… 带着一箩筐的问题,我迷糊睡去。 再醒来,已经是日上三竿了。 疲乏的身体得到了一些回复,我刚坐起来,就有在旁边待命的婢女端着水来伺候我洗漱。 真是不管在什么朝代,有钱有势就是好啊! 接着是穿上那些复杂的衣服,最后是梳头。 九千岁这儿的镜子质量明显好很多,我这才有心情仔细端详自己的脸。 可真好看啊,这可也真太好看了吧,这真的也太好看了吧! 穿越成这样真的是活一天不亏,活三天血赚啊!! 后面的丫鬟看着我一脸痴相,都不敢下手梳头了。 以前总想,古代的女人,每天多无聊了,现在才觉得真的不无聊,这起床洗漱梳头,搞搞清楚,两个小时估计都过去了。 等我梳洗完了,我以为就要去昨天那个地方展示化妆术了,谁知并没有人来喊我去,也没人理我,我自顾自往外走,也没人拦我。 在偌大的院子转了几圈,我很快就放弃了逃跑的想法,昨天被逮回来的经历是历历在目,我现在是逃不出九千岁的手掌心的。 吃过饭后,百无聊赖,我问婢女,“有纸吗?写字的纸。” 婢女恭敬回答,“有的。” 我让婢女去给我拿张大的纸来,再去厨房给我搞两块碳来。 婢女虽然不知道我要干嘛,但还是一溜烟小跑去做了,想必是有人嘱咐了她,我的一般要求都要满足。 很快,我就在桌上铺好纸,开始用大小不一的碳块开始画画。 说来惭愧,我是一个从小学画画的美术生,当年高考的时候,美术成绩也是一骑绝尘,可惜毕业之后,我看得上的工作看不上我,看得上我的工作我看不上。那时候自媒体行业刚开始火,化妆和画画从某些角度来说,比如阴影啥的,是相通的,我就去学了化妆,开始当一个美妆博主…… 在这个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世界,我能想到的也就是画画消遣一下时间,毕竟我学画画也是因为我是从小真心喜欢这个。 如果不是因为真的喜欢,难道家长真的以为可以逼我十几年如一日的练习画画吗? 我让婢女坐我面前,开始对着她画素描,这一画,就从烈日当空画到了夕阳西斜。 须伯找到我的时候,我正在画最后收尾的一些细节,须伯看了看我的画,又看了看我面前的婢女,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,“雾姑娘的画,竟可完全复制他人模样至此?” 我得意的点头,说,“你再给我点时间,我能画更好呢!” 其实,我读书时候就因画画过于写实而得到过很多荣誉,但是,随着学画画时间越长,写实的画渐渐不符合我进步的脚步,过于写实无法表达出内容,一个真正的画家,他是能去表达出很多东西的,我做不到,这是我一直的瓶颈。 但是,在这个没有照相机的时代,我这写实可就真一点都不过于了。 须伯命人把画收起,言语中已经少了之前那种敷衍的礼貌,多了几分真的尊敬,“雾姑娘,九千岁回来了,邀您前去。” 说罢,他还让人带婢女一起过去,我猜应该是要去炫耀一下我的画画技巧。 只不过,这路程远得真的有点超乎我的想象,昨晚上是九千岁抱我回来的,我半睡半醒半昏迷的状态,不知道走了多久,今天自己走过去,才知道原来这么远。 真是个臂力惊人的,太监啊! 堂上除了九千岁,还有另一个身形和他相似的人,想必就是昨天所说的那个旁系子弟。 须伯走到九千岁面前,声音中难掩喜悦,“九千岁,今日我去接雾姑娘时,正遇到她在画画,您看,画的正是这个婢女,这简直是一模一样,老奴也颇通画理,但这等画法,我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。” 就在我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技多不压身的时候,一把亮闪闪的剑架在了我脖子上。 7、 我震惊抬头,那九千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在我面前,剑刃已经割破了一点我的脖子,些许鲜血顺着我脖颈流下,染红了我的衣服。 所有人都愣住了,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 九千岁看着我,微微一歪头,说,“传闻寄语楼头牌歌姬雾弥,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我也见过雾弥现场作画,绝不是此般,你到底是谁?” 我眨巴着眼睛,冷汗一把一把的冒。 九千岁继续说,“雾弥不会易容。” 我张着嘴,“我……我……”,我了半天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…… 我的结巴直接让九千岁认定我根本不是雾弥,他说,“你是什么时候替了雾弥?” 须伯也一脸惊慌的看着我,这要是我替换了雾弥,这可就是他工作的大失职了。 我忍不住咽口水,脖子上的疼痛远不及这冰凉的剑更吓人,此情此景,我根本没办法动脑子编造故事…… 我看着九千岁的脸,想着要不赌一赌,说实话。 事实上,我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…… 于是,我鼓起勇气说,“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,但是你要让他们都出去!” 九千岁看了我一眼,招手示意须伯他们退下。 须伯他们不敢违抗,一眨眼的功夫,偌大的堂上就只剩下我和九千岁两个人。 九千岁把剑放了下来,我腿一下就软了,瘫坐在地上,摸了摸自己的脖子,虽说没割破血管,但也是流血不少啊。 九千岁看了我一眼,说,“你说吧。” 接下来,我用尽可能详细的可信的说法,说明了我是一个从另一个世界穿越来的人,我的意识占据了雾弥的身体,我和这里所有人都无冤无仇,只是莫名其妙来到了这个地方,莫名其妙生了个孩子,而现在,我表现出这么多,都只是为了活下去。 九千岁听我说完,眼睑微低的凝视着我,说,“你是说你的身体是雾弥的?” 我点头。他他又说,“雾弥的左胸下一寸有一颗朱砂痣,你且给我看看。” 说完,他遥遥伸手指了指我左胸下方。 我疑惑了一下,随即毫不犹豫开始脱衣服。 说实话,我很清楚,比起死掉,我不怕被人看光,更何况这人还是个名义上的太监,看就看吧,看了又不会少一块肉,这又不是我的肉体,我自己都不熟悉呢,再说你和这肉体造了娃,要看你也早看过了。 我脱衣服极不熟练,没办法啊,这早上可穿了好久的,我性子也急,连拉带扯的,把自己扒了个七七八八。 可我的左胸下,并没有朱砂痣。 九千岁看着我,一脸玩味,满脸写着——我看你怎么圆。 我使劲眨了眨眼,试图让自己冷静,说,“九千岁,你是不是记错了?” 谁知,九千岁笑出了声,说,“有趣,真的是有趣,天底下居然有此奇事,同人不同魂。若是你刚才有一点犹豫,你就不会站着在这里和我说话了,雾弥胸下根本没有朱砂痣。” 原来是诈我…… 九千岁看着我,问,“你当真会易容术?也会复刻他人长相?” 我点头,说,“你们说得易容术,在我们那里其实是属于特效化妆的一种,如果可以去模仿别人的话,还是有七八分相似的。至于复刻他人长相,那个叫素描,是我们那边画画的一种方法。” 我如实相告,九千岁也不说话了,半晌,他才说,“你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你不是雾弥么?” 我抬头望着他,摇头,他说,“你和雾弥,完全不一样。” 我心道这不是废话么,他又说,“今天就这样吧。” “还有,我叫路云困。” 8、 那天之后,我好久都没有见到路云困。 我没事就在屋子里画画,无聊得要冒烟了。 脖子上的伤成了一根红色的细线,也不知道能不能消掉。 转眼间,一个月过去了。 当须伯出现在我院子里的时候,我就差抱着他亲一口了,须伯看着我满屋的画像,震惊又和蔼的说,“雾姑娘,九千岁让我来告诉你一声,他明天要出远门,让你收拾一下,与他随行。” 我高兴得快跳了起来,终于可以出门了! 须伯让我选两个婢女一起,准备准备,明天一早来接我们。 这一个月以来,我和院子里的婢女也混熟了,关系最好的还是最贴身伺候我的两个,她俩听说要出门,也高兴的收拾东西去了。 第二天一早,婢女和侍卫就张罗着把东西搬上马车,须伯引着我上了另一辆大马车,我进去了才发现,里面还有两个人。 一个是路云困,另一个是那个和他长相几分相似的旁系子弟,穿着和他一样的衣服,梳着同样的发髻。 而整个马车里,有难掩的血腥味。 我走近一看,才看到路云困胸口包着层层纱布,隐隐有些渗血,忙问,“你这是怎么了?” 路云困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而是说,“你给他易容成我的样子,要快。” 我看这情形,知道此时不能掉链子,马上开始着手易容,还好这一个月的无聊时光让我做了很多肤蜡和优化后的化妆品备用,比我第一次的时候要效率多了。 不多时,我就把这小弟画好了,路云困看了之后,自己都愣了一下,随即对我说,“此刻马车刚到城外,你待会随路林下车,把他当做是我,和他依依惜别,记住,要恋恋不舍,缠绵越久越好,之后再上车,就当是送走了我,演一场戏,明白么?” 我点头如捣蒜。 路云困接着看向路林,说,“此行凶多吉少,莫正面应敌,保重自身。” 路林拱手道,“九千岁您放心,路林就算是死,也会给您多争取一日半日的。” 说完,路林下了车,随即转身扶我下车。 我没有回头看路云困,扶着路林的手下了马车,马上进入了角色,和路林在城墙外又是抱又是搂又是窃窃私语,还挤了几滴眼泪出来,殊不知,我说的全是怎么保护肤蜡维持更长时间的技巧。 上了马车,路云困看我的眼神都变了,说,“你可真是一次比一次让人刮目相看啊。” 我骄傲的扬起下巴,拍着他的腿说,“有我在,路云困,你的福气在后头呢~” 路云困想要坐起来,有些吃力,我忙去扶他,他说,“行,我等着看你给我的福气。” 我偷偷看路云困的伤,谁知他为了包扎方便,披着的外衣下面没有穿里衣,我的视线顺势从他的胸肌滑到了腹肌。 嘶……一个太监没有雄激素怎么能有这么好的肌肉呢…… 路云困看着我,说,“你现在是不是在想,一个太监怎么能有这样的身材?” 我惊讶抬头,“啊?你有读心术?” 路云困摇头,说,“你在想什么,都写在你的脸上,不过你放心,我不是真正的太监。” 我撒开他的手,说,“你不是真正的太监我才要不放心呢!” 虽然我早已经猜到路云困不是真正的太监,但却没想到他这么直白的告诉了我,我以为他不会给我解释这些。 路云困嘴唇有些惨白,说,“你不想知道我怎么受伤的吗?” 我点头,说,“想。” 路云困侧过身去不看我,说,“我不告诉你。” 我:……须伯他们知道他们的九千岁,还有这一面么? 9、 马车一路行进,我和路云困一路无言。 想到路林走时那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背影,我隐隐能猜到点什么。 当我实在是忍不住了,想和路云困说说话时,却发现他靠在垫上,昏昏欲睡,脸上有这些不正常的潮红。 真的是,一旦接受这个男的不是太监的设定,他真的是好看得让我觉得不真实。 但转念一想,我雾弥的这肉体,生了孩子腹直肌都没有分离的,比起他来,难道差了? 我叫了两声路云困,他没有反应,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,才发现是烫得过分。 这是发烧了啊…… 我打开马车门,随行的人并不多,大多跟路林去了,我认识的只有须伯。 我告知了须伯路云困高烧昏迷的事,须伯眉头皱起,说,“前方还有五里路就到墨县了,这一路随行为了掩人耳目就没有带医士,这样,雾姑娘你且顾着九千岁,我让人先快马加鞭去墨县找医士到驿馆等候!” 我正准备答应,却隐约感觉好像在暗处有人盯着我,一种不安感油然而生。 我看向须伯,又瞟了一眼旁边,小声说,“须伯,你亲自绕路去墨县,陪我演个戏给跟着的人看,路上想办法丢掉跟你的人。” 须伯明白我的意思,给了我肯定的眼神。 我立刻公报私仇,反手给了须伯结结实实一巴掌,生气的说,“九千岁不在,你个老奴也敢教我做事?” 须伯显然是被我的巴掌给惊住了,顺势假装气急了说,“你个贱婢,此路凶险,呵,我看你能活几时!” 说罢,须伯转身上马,策马往来路而去。 我余光扫到草丛里似乎有动静,我能做的就只有这样了,剩下的就看须伯了。 车队继续前进,我上车的时候,路云困不知什么时候醒了。 他看着我,也不说话,好像在等我自己交代一样。 我伸手去摸他的额头,还是很烫,真准备撤手的时候,他把我的手按在了他的脸上,说,“别拿走,凉凉的,很舒服。” 我到不在意什么男女有别,只是有些烦躁,问他,“为什么会有人跟踪我们,你到底是干啥了?你不是大名鼎鼎的九千岁么,谁把你搞得狼狈成这样?” 路云困没有回答我的话,我见他把我当外人,就要抽手回来。 谁知他就捏着我的手腕不放,我动了几下,无果,只有任由他拿捏。 眼看快到墨县了,外面开始下雨,雨越下越大,好像要把车篷打散。 我心想,这是个好机会,我撤掉了路云困拿来蔽体的外衣,披上了我粉色的斗篷,再三两下扯散了他的长发,随手挽了两下,说,“雨太大了,你待会就假扮成我,跟踪的人看不清的,我就当你的婢女扶着你这样,你走路记得曲腿低头,你太高了,不然会露馅的!” 路云困任我摆布,也不说话,也不拒绝,只是看着我,看得我心里发毛。 好在一切都按照我所计划的进行,一路无碍的到了客房,须伯和医士正在客房等候。 我能感觉路云困整个人放松了一点,更多重量都倾斜到了我这边。 拆开了纱布,我这才看到他胸口的伤,足足有我手掌这么长,深可见骨,伤口外翻,已经有感染的迹象了。 我看着这伤口,边琢磨边说,“这种,是不是要刮掉腐肉,然后缝合伤口啊?” 医士看了我一眼,说,“正是,只是这样……” 剧痛无比。 路云困闭上眼,满不在乎的说,“动作快点。” 医士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工具,我看着就发憷,转身准备走,谁知道路云困拉住了我,说“陪着我。” 我看了他一眼,说,“我怕……” 路云困失笑,说,“我都不怕你怕什么?” 我白了他一眼,说,“你不怕你要我陪干什么?” 路云困要是现在能揍我,估计我早被揉圆搓扁了,但是他现在是个病号,被我气得只有深呼吸,然后说,“你陪着我,我之后告诉你这伤是怎么来的。” 那好说,我马上脱掉鞋,爬到了床的里侧,蹲坐在路云困旁边。 刮腐肉的过程可谓是触目惊心,路云困的汗一把一把的掉,额头脖颈上的青筋都快要爆了出来,硬是一声没有喊出来,我一边给他擦汗,一边感叹麻药的重要性。 医士的动作很麻利,缝合的痛比起刮腐肉来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,我看路云困痛得有些意识模糊,一边给他擦他身边的汗,一边说,“我们那边有个故事,叫关公刮骨疗毒,就是说有个叫关公的人,英勇无比,他受伤了,需要剖开皮肉,刮掉骨头上的毒才能活。” 路云困虚弱的回了我一句,“然后呢?” 我继续讲,“当时有个神医叫华佗,他发明了一种东西叫麻药,可以让人不知疼痛,他就是给关公用了这个药,关公一边刮骨,一边吃肉喝酒吹牛下棋,谈笑风生,一点都不知道疼痛。” 刚包扎完的医士都听进去了,猛一抬头,说,“姑娘,竟有此奇药?” 我点头,说,“是的,叫麻沸散,不过具体怎么做的我不知道,我不通药理,但确实是中草药做成的。” 医士仿佛得到了人生指引,嘴里念念有词。 路云困看了看我,伸出没有受伤的左臂,趁我不注意,一把把我揽入臂弯。 医士识趣的退了下去。 我想挣扎起来,路云困却说,“你整个人都是凉凉的,抱着舒服。” 想着路云困身上的伤口,我也不反抗了,任由他抱着。 好一阵后,路云困小声说,“幸好你是雾弥,幸好你也不是雾弥。” 10、 第二天,本来想着让路云困休养两日再出发的,谁知他竟一刻不休息,一大早就继续出发。 在马车上,我给他换了药,观察了一下,伤口好像没有发炎的迹象。 中草药真是神奇啊! 我看着他,一副审问的表情,说,“说吧,你这是怎么受的伤。” 路云困看着我的眼睛,说,“是齐太师伤的。” 我还想接着问,路云困却好像乏了,竟缓缓靠到了我的身上。 我侧头看到他宽松外衣下若隐若现的肌肉线条,脸莫名红了起来。 路云困半闭着眼,声音里竟有一些绵软,他说,“你说你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?” 我应声,路云困又说,“那你能给我讲一讲,你们那个世界都有些什么?” 我回答:“你这样突然让我说,我也说不上来啊。” 路云困也笑了,说,“你们那个世界,有太监么?” 我摇头,“没有,太监这个制度废黜很久了,我们那个时代也没有奴才和主子,虽然也有有钱人各方面都高人一等吧,但明面上还是人人平等。” 路云困愣了一下,说,“你们的皇帝会允许人人平等?” 我突然觉得路云困有些可爱,就说,“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皇帝了,换了一个社会制度。” 路云困不解,但也不执着于这个问题,他不搭话,马车内就陷入了沉默。 我看他好像有些乏了,就说,“你要不要枕我腿上睡一会?” 路云困闻言,顺从的躺了下来,枕在了我的大腿上,我牵过毯子,给他浅浅盖上。 路云困看着我,说,“上一次这样枕在女人腿上,还是幼时,和母亲父亲一起出行,我累了,就枕在母亲腿上小憩,父亲怕母亲忙不过来,就抱着妹妹骑马玩去。” 路云困还有妹妹? 马车有些颠簸,毯子盖得不是很稳,我伸手压住毯子的角,路云困却突然伸手握住我的手,我不解的看着他,他闭眼间,眼角似乎有泪。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,只轻轻搂住路云困,哼起了歌。 借一方乐土让他容身…… 借他平凡一生…… 不知道为什么,我觉得路云困不想当九千岁,也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,是个要谋朝篡位的人,哪怕现在他似乎就在做这件事。 我甚至觉得他就是一个想要有个容身之地的,平凡的孩子。 我低头浅笑,我会觉得杀人如麻的九千岁是个孩子,我也是脑子坏掉了。 低头时,我看到路云困在看我,他的眼神里有我看不清的东西。 不是九千岁的冰冷,不是杀伐果断的无情…… 是一股让我不知道如何去抗拒的吸引。 鬼使神差的,我低头,吻上了他苍白的嘴唇。 浅浅一吻之后,我准备抬头抽离,路云困却勾住了我的肩膀,起身一揽,不知道怎的,我翻身跌入他的怀里。 “你的手……”还没来得及关心他受伤的手臂,就被他居高临下的吻压得再也发不出声音。 他的吻很用力,仿佛要吸走我的所有的生命力。 我无法思考任何事情,我只能用尽我所有的思维,所有的情绪去接受他,去感受他,去融化在他的怀里。 这一吻好像吻了很久,又好像只有那么一瞬…… 神魂归位,我第一反应是去检查路云困的伤口,还好,没有裂开。 路云困看着我着急的样子,伸手摸了摸我的脸,说,“没事的,不疼。” 我抬头看着路云困,此刻,须伯在马车外轻语,“主子,已到回声谷。” 我不知道回声谷是哪里,路云困起身准备下车。 我担心路云困的伤势,他回头看了我一眼,说,“你去汝州等我,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” 看着没有解释,直接远去的路云困,我摸了摸自己的嘴唇…… 九千岁,终究,不可能是我一个人的路云困…… 11、 我有些力竭,不是因为别的,而是因为,我好像真的爱上了路云困。 这个马车里都还有他的味道,淡淡的。 我抱着毯子发着呆,任由马车带我远去。 随行的人除了我的侍女,我也就认识须齐一个人了,他骑着马走在最前面,看样子须伯已经跟路云困走了。 干.他们的大事去了。 是夜,我们露宿山野。 第二天,日上三竿之时,有一队人马拦在了我们车队前面。 我好奇伸手去开车门,外面却传来打斗的声音,中间还伴着有人惨叫。还有人大喊,“路云困已死,余党伏诛!” 我吓得不敢乱动,一时间不知道是下去好还是躲在车里好。 这时,一双带血的手拉开了车门,是须齐。 须齐一把拽住我的手往外拉,大喊,“出来,跟我走!!” 我条件反射的选择相信他,钻出车门,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那俩婢女横尸车前。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…… 须齐没给我任何伤春悲秋的时间,一把把我拽上马,自己飞身坐在我的背后,一鞭子下去,马匹吃痛,撒开蹄子狂跑。 身后有人在追,流箭从后面射来,须齐大喊,“趴低!” 一支支流箭从我耳边划过,我害怕极了,尽可能的伏在马背上,祈祷马儿跑得更快一些。 好在这匹马仿佛是有灵性,一直在自己找路走,看似穷绝的道路总能让它找到新的出路。 不知跑了多久,我才看到,我们又回到了昨天路云困走的地方,回声谷。 马儿也有些累了,追兵早已不见踪迹,须齐让马走得慢了些,我这才看见,须齐肩膀中了一箭。 我看着须齐的肩膀,有些惊慌,毕竟现在整个车队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 须齐倒是反手就把箭头砍去,毫不在乎的说,“无妨,小伤。” 马儿识路,没有走回声谷的大路,走的竟是一条根本难以发现的小路,前面走的那段路还算是天然形成的,中间有些地方带有人工凿做的痕迹。 傍晚时候,马儿带我们到了一处不起眼的田庄,而这田庄后面,就是都城城墙。 我们马车行进了一日多才到达了回声谷,回声谷回到都城走这小路竟不需半日。 怪不得路云困要在回声谷下车,那路云困应该昨天中午就已经回到都城了。 我脑子乱作一团,所以,我们第一日从都城出发,第二日中午路云困就回来了,现在是第三日傍晚。 而刚才来杀我们的人,大喊的是,“路云困已死,余党伏诛……” 路云困死了。 12、 这个念想仿佛揪住了我的心脏,难以呼吸。 路云困昨天回去的时候还是伤重的状态,对方又不是软柿子,所以他真的有可能…… 夜色茫茫,前路也茫茫…… 田庄中什么人都没有,须齐藏好马,熟练的找出伤药,看我在发呆,招呼我过去帮他。 箭伤不深,拔出箭之后帮须齐上了药,我忍不住问,“路云困是不是出事了?” 须齐看着我,眼神里也没有了光,说,“我不知道,九千岁给我留下了这匹马,只说如果有任何变数,定要护你周全,其他的,我也不知道。” 护我周全…… 须齐找到屋中的一处机关,推动后,出现了一个地道,转身招呼我说,“走吧。” 我问他,“去哪儿?” 须齐说,“按照九千岁的计划,我们回来之后,带你去安全的地方。” 我跟着须齐进了地道,走了很久,久到我都以为自己鬼打墙了,终于到了出口。 而出口,竟是在我最初逃出的那家客栈的酒柜后面。 怪不得我当时刚出来就被抓了回去,居然这里也是路云困的地盘。 须齐把我安排在了一间隐藏屋里,屋里有干净的衣物和水粮,即便是外面搜这个客栈,也很难发现这里有个屋子。他交代我不要离开这里,自己却转身进入了黑夜里面。 自此,我身边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,醒的时候,天已经亮了。 客栈里有人说话,我这才发现我这个屋子的一面墙正好是贴着客栈一楼餐桌区域的,其中一个男的说话的声音尚有余悸,他说,“你看到了吗?九千岁的头,就插在城墙上面呢!”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,几乎站立不稳,路云困死了? 另一个男的接话,“他也有今天,死太监活该!你还叫他九千岁?这世上再也没有九千岁咯!” “齐太师杀了这个死太监,倒是做了件好事。” “得了吧,你见过齐太师的府邸嘛?就算你读一辈子酸书,都不够买他门口那块垫脚石的。” “是啊,杀了这个九千岁,谁知道会不会有下一个九千岁呢?” “依我看,何为九千岁?那是因为他没根,当今圣上如此孱弱,怕是有根的人,都不甘为九千岁吧!” “王兄!慎言啊!” 我靠在墙边,这齐太师怕不就是那个伤路云困的人么…… 路云困死了…… 我手脚发凉,我不信路云困就会这样死了,我要去城墙那里看看。 剩余42%未读立即解锁专栏,阅读全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shenjincaoa.com/sjchq/12374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民间故事男子去放牛,见妇人落难相助,妇人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