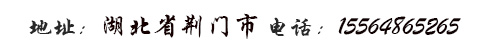我救了一个身受重伤的男子,用尽了平生的力
|
大医院治疗白癜风 http://www.znlvye.com/ 1 三月多雨,朗了三天又是一阵大雨,天微朦胧便雨打梨花。我伫立窗前欲关上窗户,却瞥见门前的梨树下似有一人躺卧。 顾不得深究,撑伞前往。 梨树下躺着一个男子,豆大的雨滴砸在他身上,一席白衣已经污浊不堪。他双目紧闭,面上毫无血色。久病成医,我知他受了很重的伤。 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拖他回屋,我累个不行。摸了摸脉搏,还有些生气。换了他一身脏的不成样子的衣服,瞥见他背后与脑袋上的新伤,不由得有些心虚。 阿姐说,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舅舅与舅母不知前路如何,阿姐闭关不知能否突破。我如今救他一命,只求这份福报落在他们身上。 近来多雨,好不容易得了一天的太阳,我将收进屋中的药材一一晒在院中,回来看见那人已半起身。 我与他四目相对,他的眼睛很漂亮,像是我养过的一只小雀。 我道:“我救了你。” 空气仿佛沉默了,好半晌,他道:“多谢。” 簸箕中的药材被我拾掇着发出轻微声响,我提高了声音:“你伤的有些重,这几日还是不要下床的好。若没有急事,还是在此地休息些日子吧。” “好。”他又慢慢地躺了回去,“不知如何答谢姑娘。” “举手之劳,”我又忆起福报这件事,“你若实在过意不去,不如伤好后替我摘些药材。” 他身上的伤很是复杂,费了好些药材。且天公不作美,落雨后山路崎岖泥泞,很难令人愿意前往。 “全听姑娘吩咐。” 厨房中“咕咕咕”的声音唤回了我的思绪,急忙奔向那刚被热乎好的汤药,回来时还带了一碗粥。 “空腹喝药不好,吃些粥垫一下。” 他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,直愣愣地看着我。 我道:“现在可以起身。” 他的声音中似乎有些无奈,“刚才起身废了太大的力气,如今没有力气了。” 我只好扶他起来。 一阵缄默后,我又认命的喂他喝粥。 他垂下眸,“麻烦姑娘了。” 他的睫毛很长,眼睛眨动时像是一片羽毛在你心中轻轻地扫,痒痒的。 看着他如此乖顺,我又温柔了几分。 “不曾问过姑娘姓名,能否告知于我,日后好做答谢。” “我叫阿箬,箬水青似箬的箬,你呢?” “萧恒。秋风萧瑟的萧,无恒安处的恒。” “好名字,萧恒。” 我眉眼弯弯,对他一笑。 观今日天色,夜晚无雨,我便将药材草草的盖上一层薄布。待月上柳梢时,我悄悄潜入了萧恒的卧房。 欲结阵之时,有一声音打断了我,“阿箬姑娘?” 我面色僵硬,“是我。” “不知姑娘有何要事?” 隔着墨色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,我点起烛火,走到他身前,“我过来看看你是否睡的安稳。” “多谢姑娘挂念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“我睡眠浅,听见姑娘的脚步声才醒来。” “......”“打扰了。” “无妨,”他眉眼温柔,“是我应该感激才是。” 阿姐曾买了一本俊美男子传,我翻阅了许久,但我觉得画图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如他来的好看。 我一下子溺在他的眉眼中,突然觉着,熬药与喂药也并非是一件苦差事。 2接连照顾了萧恒三天,在我对他的美色免疫欲再次结阵之时,他终于行动如常。 他伤好些后很是勤快,三餐皆由他来准备,我自小只会一些简单的家常菜,阿姐、舅舅与舅母不在时饿不死就好,如今有了不小的口福。 平日里,也会过来帮我一起摆弄这些药材。 他会耐心地询问我:“阿箬姑娘,可有我需要帮忙的地方?” 四月梨花朵朵开,若将梨花做成一些梨花膏,也是极好的药。 我拜托他摘一些梨花,不过一会儿,就有一大盆,好在梨树并没有被他作弄的秃了。 我照着书中的法子一步一步来,瞥见他嘴角隐隐有些笑意。 他本就生的丰神俊朗,如今不禁令人心神荡漾。 我问:“想到什么开心的事了?” 他反应过来我与他说话:“我有一好友,出自制香世家,平时看上去有些蠢笨,但在制香上,却一点也不含糊。” “如今看你这般精细,不由得想起他。” 制药与制香的内容虽大相径庭,但万变不离其宗。我有些好奇,“你那好友,如今在何处?” “大约于万花阁、烟雨阁之中流连,他自诩风流,万花丛中寻风月。” 我停下了手中的活,不由得来了兴致,“万花阁、烟雨阁是做花草营生的吗?” 他沉默了一瞬,脸色有些微微泛红,“并非...如此。” 我一时之间有些不解。 他看上去似乎有些狼狈,“不说这个了,可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?” 我将梨花盆端放侧边竹架上,掸了掸旁边的石凳,示意他坐下,“今日不做其他,我想听听外面的故事。” “外面的故事?” 家中只有舅舅的男子衣服,好在有几件宽大的,他穿着也算合身。 衣服带着一丝药香,隐匿在这药屋中,而隔着衣服另一种冷冽的气息怎么也挥之不去。 随着他一落座,也静止了。 “我自小就在这个小屋中,去的最远的路就是山上的林子,从未去过外面,我身体不好,不宜多行。” “我也希冀着能同阿姐那般持剑而行,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。” “不如你讲与我听吧。” 我期待着注视着他的眼眸,渴望从中听到我想要的答案。 不知过了多久,他问:“你喜欢听什么?” “阿姐说,世间不过风花雪月,快意恩仇。你就讲讲遇见的趣事吧。” 他略一思索,“江湖有一榜单,名唤英雄榜,乃落玉门所列。上月榜上排名第十的竹溪先生身故...” 我与他落座时太阳正好,如今已日薄西山。 他的声音低沉,故事娓娓道来,我感叹,“竹溪先生真是又可恨又可怜。将自己的亲生孩子认作妻子与道君所生,折磨了二十年,真相大白时孩子寿数无几,又散尽全身修为救他一命,留得自己陨落的劫数。若我为他儿子,怕是究其一生都要治愈这伤痛。” 薄薄的一道霞光掠于几片白云之上,彼时他正讲到温衡公子尤爱万珍楼的龙须酥,我不由得有些饿了,抬头看向他的眼睛,“我也想去尝尝你说的龙须酥。” 那日的霞光也同样蒙蔽了萧恒的双眼,他笑道:“好。” 龙须酥的原料并不复杂,不一会儿就凑齐了。 他将饴糖倒入锅中,用铜勺搅拌:“龙须酥的精髓在于糖的熬制,若它成型的好,就成功了一大半。” 我好奇地凑近瞧,被他拉开,“高温熬糖,你小心。” 待糖熬制的差不多了,他将糖放入托盘上,静候放凉。 凉了的糖像是琥珀色的露珠,晶莹剔透的。 将糖裹挟成圆形反复横拉直至成丝状,再裹上面粉,洒上一些芝麻,就做好了。 或许是练过武的原因,他横拉糖时速度极快,不一会儿就成型了。 做好的龙须酥模样好看,放入口中即化,丝丝甜意弥漫舌尖,让人不禁雀跃。 “好吃!”我不由得夸赞,我素来爱吃甜食,如今这龙须酥完全踩在了我的心口上。 “萧恒你真厉害!”我不吝啬我的夸奖。 “简单的一道甜食而已,”他不在意地笑笑,“等你出了山,你会发现比我更厉害的人。” 他的目光眺望窗外,有些深沉。 “但你还会讲故事!”我拉回他的视线,“你会做菜,又会讲故事,是我平生见过最有趣的人。” 他失笑,“你才见过几个人?” “你是第五个。” 我又细想了一下,“不对,若算上阿姐给的那本画册,你算第个。” 萧恒笑出了声,眉眼上都染上了笑意。这是我与他相处多日来,第一次露出开怀的表情来。 我一时将心底的话说出:“你多笑笑,这样好看。” 我们于酉时动手,如今已至定昏,窗台上的烛光被微风吹散,萧恒未动,一侧脸颊的光影轻轻晃动。 他欲拿起一块龙须酥,又轻轻放下:“时间不早了,早些休息。” 又下了几日雨,迎来了明媚阳光。有几味草药逐渐见底,需要采撷新鲜的。 我给他一幅图,又告知他,“大约入林千米处,往返一趟一两个时辰足矣。” 他立马就去办了。然而过了三个时辰也不见回来,我怕他出现什么意外,急忙赶往林中。 3昨日刚下过雨,山路有些打滑,我尽量小心,却掩饰不了内心的焦急。 “萧恒,萧恒...” 我大声呼喊,盼听到他的回应。 入林已有千米,却寻不见他身影,又继续向前。待行至一溪水旁,于右边山洞中传来他回应的低微声音。 洞中,他浑身发抖,嘴唇惨白,几缕湿发贴在他的额角,虚弱的不行。 甫一摸他脉象,暗叫到不好,中了噬蚁草的毒。此事也怪我,白笼草与它长的极为相似,只是二者所生长的位置相隔有些距离,我以为他碰不上,仍是大意了。 庆幸的是我让他采摘的药草中恰好有一味药材为噬蚁草的解药药引,配合上解毒丸,没有性命之忧。 只是他毒发之时,拼命用内力压下毒素,但噬蚁草的毒性像是弹簧,你压的愈深,反弹的越厉害。 如今,也唯有这一个办法了。 我喂他解药,结好药阵。大约是过于耗费体力,便沉沉睡去。 醒来之时,正见他触碰着阵法,“这是,”他有些错愕,“药阵?” 这轮到我惊讶了,我将舅舅的所给残本孤页还原了很久,才得出这一个又一个的药阵。未曾想,普天之下还有人认得这些。 “你识得?” 他摇头,“猜测而已,这阵法给予我源源不断的治愈之力,也唯有书中曾提过的药阵才有此等效果。”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,揉了揉肩膀,无意间道,“你初醒之日,我本也想为你结阵,恢复的更快一些。未曾想你突然醒了,我就放弃了。” 他疑惑,“为何?我并非生命垂危之际。” 我摸了摸鼻尖,“这是治愈之阵,与我那日想结的速之阵不同,”顿了顿,“速之阵能量微弱,我不过是想你好的快一些,这样就不用给你熬药喂药了。” 他竟是低低的笑了,“还好那日我醒了。” 我一时被他的笑容蛊惑住,没听清他说了些什么,“你说什么?” “没什么,”他撩了撩袖摆,“姑娘身怀如此绝技,世间有心人不少,万不可对他人再次显露。” 舅舅也曾同我说过,世间有天赋修习阵法之人甚少,更甚者是修炼药阵之人,得一人则他人趋之若鹜。 “那你呢?” 初次相见,我并非鲁莽之人,将我所学秘术显露,只是如今到了非此不可的关口。 “姑娘救萧恒性命,萧恒定当守口如瓶。” 他的语气坦荡,眼神清澈,此情此景下,我已然信了十分。 “好。”我拉起他的手,如阿姐每次下山给我带回糖糕勾手约定的诺言一般,“若你伤愈后回去,万不可与他人提起我。” 指尖相触,诺约已成。 世间良药许多,也没有立马让人活蹦乱跳的药,百般无聊下,我道:“左右你伤未愈,不如就再给我讲一个故事。” 他思忖良久:“今日就讲一个关于莫阁第十一杀手丽娘的故事。” 前几日他讲道,莫阁是江湖中最隐秘的杀手组织。黑白两道都甚是忌惮,他们还有着最灵通的消息网,不论哪家的秘辛都略知一二。 我奇道,“莫阁既最隐秘又最灵通,自己家杀手的事倒流传于世了?” 他瞥我一眼,“听不听?” “听,听。”我笑着狗腿。 “丽娘在江湖上素有着‘艳姬’的称号,她生的容貌昳丽,菩萨面容手段却是毒辣。一日执行任务时,不慎遭人暗算,却被一白面书生所救。” “书生不懂得江湖事,知节有礼,赤诚热忱,还有些书读多了的呆子气,见到美人的傻子气,靠着结结巴巴的话语拿下了江湖大名鼎鼎的‘艳姬’。” “丽娘欲与他退隐,从此相夫教子,山水不相逢。但背叛组织的,从来都是死路一条。” “他们死于一个雨夜,血水弥漫了整条街,死前双手紧握,不曾分离。” 他的语气似乎与平常无异,但我却听出了不同。 “你似乎有一些悲伤。”我道。 “相爱的两个人同死,是有一些遗憾。” “不。“我摇头,“不一样,以往你给我讲的这些故事,你都像是一个旁观者,只有这个故事,你仿佛亲眼看见一般。” 他就这样直直地看着我,并无任何情绪,我只好也这样看着他。 半晌,他背靠在石壁上,避开我的目光,略显慵懒,“你说的不错,我看到了他们的死,还是死在他们莫阁的一个杀手手中。” “是谁?” “莫阁排名十九,双刀隐月。” “丽娘排名十一,怎么会?” “他们夫妻二人中了毒,纠缠了一番还是死在隐月手中。” “现在,莫阁十一是隐月了。” 我不明白,他耐心地解释了一番,“莫阁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若是排名靠后的杀手杀了排名靠前的杀手,可替代他的位置。” “那排名第一的那人岂不是很危险,有太多人想来杀他。” “最近没有这样的烦恼。” “为何?” “莫阁正在扩大,不允许内部斗殴,只允许剑指背叛莫阁的人。” 我点了点头,问:“莫阁排名第一是谁?” “江湖名唤白衣。”他瞥了我一眼,继续道,“使剑,剑名青霄,他出现时穿一袭白衣,戴一獠牙面具,从没有人见过他的容貌。” “为何?” “与他交过手的,都死了。” “他真的从未有过败绩?” “据我所知,从未。” “他真厉害。” 萧恒嗤笑一声,“黑白两道都退避不及的人,你竟上赶着夸赞他。” “这是事实,这世间应该没多少人能打过他吧。” 他思索了一下,“有几个。百令门的天机老人,穹顶派的君柳衣,华严宗的逍遥尊者,风雪城的浪云大师,以及琴剑山庄的鸿蒙剑仙。” 数个人名砸晕了我的脑袋,我越发兴奋,“这些又是何人?你再同我讲讲呗。” 一缕阳光从洞外照进,大约第二日日中了,他起身,阳光穿过他的指尖,“我已经好了大半了,不如回去我再同你细细将来?” “好。”我笑着看着他,“听你的。” 约莫是过了下雨的日子,一连多日,都甚是晴朗。 明媚的阳光令人心情愉悦,药香弥漫中还有少男少女的絮絮。 萧恒的伤势渐渐好转,不出三日他也用不上药了。 十七年来,头一次觉得药效太好也并非一件好事。 我再也没有理由留下他了。 午时收拾饭桌时,我不慎将一只碗打碎,收拾时又不小心伤了手。 他听见声音后立马过来为我处理伤口,“还疼吗?” 我的指尖与他的指尖交叠,一股热意让我想逃却逃不开,逐渐地有些贪恋,我克制地缩回手,“小伤而已。” 他又拉过我的手,“是你说小伤不理会成大害,你可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。” 我望着他,眼中是化不开的愁绪,欲言又止。 他注意到我的神色,手中愈发轻柔。 我再三做心理建设,仍是不敢开口,只得在心中长叹。 午后在那院中,他问我,“今日想听些什么?” “讲了太多旁人的故事,今日你能不能讲些关于你自己的?” “我没有什么故事,我的人生很无聊。” “随便讲一些,你爱吃的,你喜欢的,或者家在何方,若我以后走出这山了,也可以寻的到你。” 半晌也未听到他的回答,我不敢看他的眼睛,只不停的捣弄着手中的药材。 “我于洛阳城北街处有一萧姓宅院,若你来寻我,我必以最高礼仪相迎。” “当然,”我笑着看向他,“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” 我又吵着他做一次龙须酥,在完成时,我对他说,“明日,最后帮我摘一次草药吧。你伤已经痊愈,明日后,我们便两不相欠了。” “好。”他看着我,“芝麻可少洒一点,多了不好吃。” 或许是我内心过于逃避这一天,我起身时他已去了山林中。 我百无聊赖的摘掇那些药材,摘一会儿又驻足片刻,一日下来什么也没干成。 天色渐暗,他仍没回来,一如那日般,我慌张地去寻他。 他又中了噬蚁草的毒,歪倒在山洞中不省人事。 我结了药阵,体力耗尽后与他一同沉沉睡去。 4待第二天天明,他醒的比我早一些,见我醒了,他的嘴角似有一丝苦笑,眼中的情绪是我不曾看明白的。 “你又救了我一次。” “我又欠你了。” 不知怎的,我突然向前抱住了他,这大约是我十七年以来做的最出格的一件事。 “那你,以身相许,留在此地一直陪着我,好吗?” 我的声音颤抖着,已然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。 他的双手回抱住了我,抚平我内心的颤抖,回答我的低沉的声音掷地有声。 “好。” 从洞中出来时,我仍脸颊发烫,羞涩的不敢言语。 他握紧我的手,也再也没有放开了。 从林中回屋,这段路漫长又短暂,我将思索了一路的想法说了,“萧恒,我们成亲吧。” 他向来喜行不于色,平常也仅是淡淡的笑意,竟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了懵的神情。 “你曾说成亲是一男一女双方共同生活,如今我们也算是一同生活了,补一个成亲的仪式吧。” 萧恒顿时哭笑不得:“阿箬你可知,成亲规矩复杂...” 我打断了他,“我们生在天地间,定然也要如江湖儿女般,不拘小节。” “我们叩拜天地,叩拜日月,叩拜山川,叩拜林木,叩拜溪流,还有门口那一颗梨树,让它们为我们做媒,结良亲成良缘,共赴余生。” “萧恒,好吗?” 眼含笑意,满眼都是那一人。 他向来更喜欢用行动来回答我。 他执我之手,跪拜过天地、日月、山川、林木,剪了我一缕头发与他的一缕头发用红绳打成结。 “愿上天垂帘,护我们一生安康。” “萧恒与阿箬,结发为夫妻,恩爱两不疑。” 今日他做了一大桌子的菜,我还拿出了舅舅的珍藏好酒。 “舅舅他从来不让我喝酒,说是对我的身体不好,但今日是我的喜事,我要多喝几杯。” “萧恒,你之前的故事中说道,成亲二人要喝的是什么酒来着?” “合卺酒。” “对对。” “我们来喝一杯。” 我给他满上,抬手欲喝下自己手中的酒时,他制止住了我。 我不解,他牵过我的手,与我的手交错:“才这是合卺酒的正确喝法。” 民间合卺酒寓意夫妻间相互扶持相互缠绕,阴阳相合天覆地载。他亦有私心求一个永不分离的未来。 我们的头离得极近,一杯酒喝下,不知是酒辣呛的缘故,还是这气氛的渲染,我的脸极红。 慌张下,我又喝下了一杯酒,这次,大约是真的醉了。 我极不清醒地抱住了他,“萧恒,你不要离开。” 语气是平生未曾有过的娇气,萧恒失笑,“你喝醉了。” “没醉没醉。” “你答不答应我嘛。” 我的眼神迷离,感觉天地都在晃动,他抱起我,“会的,我会与阿箬一直在一起。” 他抱我到床上,我却感受到了他的离开,我拉住他的袖子,“阿恒,我们都成亲了,不是应该睡一起吗?” 我用尽力气拉他躺下,“别走,我们一起睡。” “卧房很大的。” “不会挤的。” 迷迷糊糊间声音越来越轻,就渐入了梦乡。 萧恒握紧了拳头又缓缓松开,呼吸急促了几许又慢慢平静下来,他轻触旁边之人的鬓发,指尖轻柔,满眼是宠溺。 他捻好被子,倒也不曾离去。待至夜阑三更,却也不曾入眠。 5第二日我醒来时已近午时,仅两杯酒竟宿醉的如此厉害。 萧恒端来饭菜,示意我起来吃饭。我揉着有些痛的肩膀,“阿恒,等下同我去山林中摘些草药吧。” 菜入口的时候,我才意识到自己喊了什么。 阿恒...如此的亲昵。 他神色如常,并未觉得有何不妥,点了点头继续为我夹菜。 许是我良久的沉默换来了他的注意,他意识到了,“无妨,你喜欢喊什么就喊什么。毕竟,你我已是夫妻了。” 昨日一天的回忆向我砸来,羞红了脸。 我糯糯地开口:“郎君。” 萧恒夹菜的手一停,“嗯”了一声,脸色并无异常,耳朵却渐渐爬满绯红。 自萧恒出现以来,我所需要的药草都由他寻来,很久未去摘过新鲜的药草了。 路过门口的梨树时,我突然想到,“阿恒,你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梨树下?” 陶然山地处偏僻,已经很久未来人了。 他回我:“我寻了一个僻静地方修炼,不慎走火入魔误打误撞来到了此地。” 我有些心疼,“我只见过阿姐练剑,武功修炼我也不是很懂。但修炼如此凶险,你不要练了好不好?” 我巴巴地看着他。 他撩开吹落在我脸上的头发,“你说想要去江湖上看看,江湖凶险,若不好好修炼,我如何能护的住你。” “我们可以雇一个保镖嘛,”我想了想,“请动莫阁第二的杀手需要白银千两,我们就用白银万两请更厉害的莫阁第一。” “不知卖了这一屋子的草药值不值这些钱...” 我打量着满屋的药材。 “不用,你只需要勾勾手指,他就欣然前往。” 一阵风吹的梨树叶沙沙作响,我没听清他说了什么。 “你说什么?我没听清。” “我说,莫阁里是一帮杀手,接的都是杀人的任务,不如寻其他人吧。” 我笑嘻嘻地回他:“但有莫阁第一在,别人就不敢动我们了。” 那一笑容晃了萧恒的心,他勾住了身侧之人的手,“走吧,再不去要天黑才能够回来。” 夜晚,我洗漱好后等着萧恒一同过来入睡,却左等右等不见他身影。 只好披了衣出去寻他,他正在院中眺望天上的月亮,我拉住他的手往房间走去,“夜凉如水,该睡觉了。” 回了屋,我脱掉披着的衣服,转身上了床,欲示意他快些,今夜入睡的有点迟了,有些困意。抬头却见他的眼眸中有化不开的墨色。 我隐隐有些害怕,只好开口唤他,“阿恒...” 他一步一步朝我走来,我却怎么也说不出其他的话。 他低下头,伸手搂住我的头,双唇与我的双唇相碰,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,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我胸口蔓延。 “今晚我再给你讲一个夫妻之间才会发生的故事。” 他附在我的耳畔,声音是从未有过的沙哑。 不待我回答,他又触碰上我的唇,接下来的时间,完全由他掌控。 等到第三日我才醒来,他着好衣冠在我身侧,我偏过头,不想理会他。 他低声哄我,“你已经一天未进食了,吃些东西吧,对身体好。” 见我不理他,又轻声哄我,“阿箬,好阿箬,别生我气了。” “下次...” 我转过身狠狠地瞪着他,开口的声音十分沙哑,“哪还有...” 更生气了。 “我的错,我的错。” “你的身体不好,吃些东西吧,好不好?” 我终于还是吃了几口,起身间又扯动了疼痛处,便又瞪了他一眼。 这一眼对萧恒来说毫无威胁,颇有些娇嗔的意味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萧恒也很知分寸,每日弄些药材,煮些食物,讲些故事。 两人一屋,便是全世界。 6日子就这么有条不紊的过着。及至六月下半旬,那天,我一直都记得。 六月少雨,二十三日却下了好大的一场雨,狂风大作,电闪雷鸣。 我醒来时寻不见萧恒,只看见他留的一封书信,“有要事处理,解决后回,勿念。” 我捧着这张纸久久不能回神,明明昨日我与他说道,七月五日是我的生辰,阿姐、舅舅和舅母过几日定会回来,到时候定要让他们好好瞧瞧我的郎君。 他笑着说好。 今日却不见了。 其实近半月来,隐隐有些感觉,他总会莫名其妙地愣神,我只当他劳累了,现在回想起来,一切皆有迹可循。 我坐在镜前,努力给自己一个微笑,但比哭还要难看。 我每天地等着。 及至一天,外面有声音传来,“阿箬,我回来了。” 是阿姐。 “阿箬?” 她推开门,看见我在一片阴影中。 “阿箬,你怎么了?” 我转头看向他,“阿姐,他好像不会回来了。” “谁?” “阿箬?” 阿姐在耳边唤我,我却渐渐地听不见了。 醒来时,舅舅与舅母也在,只是他们的脸色并不好看。 舅舅哀叹了三声,开口的话确实惊天霹雳,“我已经传书给你父亲,三日后他便来接你。” “我不去,我要在这儿等他。” 他并不询问我口中的他是谁,只是握紧了拳头,指尖泛白,半晌,才平稳自己的气息。 “阿箬,你怀孕一月有余了。” 我蠕动嘴唇,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声音。 “你父亲有钱,也有能力搜罗各地的滋补之物,你且去那儿安心养胎,你放心,我和你舅母,阿姐也会一同前去。” “...”“好。” 舅母替我捏好被角,温柔地揉了揉我的脑袋。 阿姐欲言又止,终是不忍心打扰我而离去。 这几年来我见过我的父亲,他独自来陶然屋看过我,他生的威严,对我很是慈爱。 第三日清晨的鸟雀一鸣,陶然屋已然来了许多人。也许是怀孕的缘故,我嗜睡到巳时才醒。 一睁眼就看到了父亲。 他有些沧桑,许是赶路未曾睡好。 “阿箬...” 他欲触碰我,又不敢触碰我。 万千言语化作一阵叹息,“有我在,以后没人敢欺负你。” 我被阿姐和舅母扶着出门后,才发觉舅舅口中的有钱可能有些保守了。 浩浩荡荡一堆人,看不到尽头,比我前十八年以来见过的人多了数倍。 我坐上备好的软轿,里面的空间异常大,备着丰盛的水果糕点。 如此琳琅满目,我低声问舅母,“父亲,究竟是什么身份?” 舅母为我沏了一杯水,答道:“你父亲,是天驰国的国君。” 我心中大约是弹了一首乐曲。 “你母亲,名唤楚卿卿,是前任天驰国宰相的嫡女,幼时拜入百令门,成了天机老人的小弟子。” “她年轻时闯荡江湖认识了微服出访的你父亲,相识相爱,二人定了终生。你母亲怀孕后,你父亲将她接回宫中。” “她长于江湖,自由烂漫。宫中的条条框框压的她喘不过气,郁郁寡欢下生了你后就走了。” “你舅舅从小就疼爱这唯一的妹妹,不足月生的你又小的可怜,在那深宫中如何存活的下去,只好仗着药王亲传弟子这一身份强行将你带走,安置在陶然山。” “这就是往事所有的前因后果了。” “你父亲对你有愧,但也并非不爱你,该如何面对,你自己决定就好。” 犹记得小时第一次见到父亲,他带着小心翼翼,一如现在般。 作为孩子我理解与他多年来的分离,但我无法站在母亲的角度上,与父亲和解。 爱嗔痴,恨别离,往事不可追,如今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平安生下这个孩子。 父亲给的住宅很是豪华,也很清净,除了几个仆从,无外人打扰。 安顿好后,我坐在庭院中,眼神焕然,无意识地看着方寸土地上方的蓝天白云。 视线中出现一支竹蜻蜓,晃悠悠飞在空中。 余光处出现抹白色身影,“你的二九生辰已经过去了几天,阿姐未送上礼物,今日补给你。” “阿姐。” 我抱住她,不免哽咽。 “痛痛快快哭一场,以后可是要当母亲的人了...” 父亲每日都给我送了很多补品,在舅舅与舅母的照顾下,身体胖了不少,肚子亦是。 养胎的日子就这么过着,仿佛从前那般。 一日我正在数着院前树上的叶子,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静谧。 “我倒要看看父皇...” 一双略显眼熟的眼睛与我相对,但面容却大相径庭,是我未曾见过的。 “你是谁?”他问我。 “那你是谁?”我又问他。 拦路的宫女不停跪下哀求,我大约明白了,或许是我的哪一个哥哥。 我示意她们离去,又看向他。 “坐”,指了指我身旁的空位,“今日恰巧无事,不如闲聊几句。” 他大方落座,问我:“你是谁?” “你呢?” 又重复了之前的问答。 “我是天驰国的二皇子,商泽。” 坐久了有些不舒服,我扭动了下身子,“算起来,或许是你的妹妹。” “妹妹?你是父皇的女儿?” 我点了点头。 “我以为...以为你是...”他艰难地开口,“父皇的妃子。” 我嗤笑他,“就算我是,你如此闯进来,也并不礼貌。” 他憨憨地挠了挠脑袋,“抱歉。” “父皇自德妃去世以后再也没纳过妃,一时之间有些好奇...” 他仔细看了看我,“说起来,你与德妃的面容还真有些相像...” “逆子!” 下人的通报声未响起,未见其人,先闻其声。 “父皇。”来人一来,他就毕恭毕敬,耷拉着脑袋还有点像鹌鹑。 “你在此地做什么,还不快回去。” 萧泽向前走,经过父亲身边时又退了一步。 “父皇,妹妹既已回家,你为何不昭告天下呢?” “父皇可听见外面谣传乱飞,说是您养在外面的妃子。” “谁再乱传,看我不诛他九族。” “等等,“突然意识到了什么,”你上一句说了什么?” 他清了清嗓子,重复道:“父皇,妹妹既已...” “谁告诉你的?” “我说的。”我答。 一旁的鹌鹑亦点了点头。 已年过半百的国君这一刻的眼神中涌现出明亮的光彩,“阿箬,你...” 我缓缓起身,朝他行了一礼:“父皇。” 7自我入住以来,他日日来看我,点点滴滴拳拳之意,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。 人生不过如此,短短数十载,放过自己,也放过他人。 他抚掌,“好,好,好,我这就去备下旨意。” “父皇,”我喊住他,“孩子月份大了,不如等临盆后再说吧。” “好,好,好。” 又聊了些家常话,临行前,萧泽看了看四周,问我,“怎么不见妹夫呢。” 氛围有一时的沉默,父亲剜了儿子一眼,谁也没说话。 “他死了。”我淡淡开口。 刚来洛阳王城这几日,我便满心欢喜地让阿姐去找北街一处萧姓人家,得来的答案是没有。 我不信,欲动身前往。 阿姐拦不住我,带我走遍整个北街,也未有一家萧户。 我关在房中半月。 细细数来,我与他成亲数月,我竟不知他籍贯何处,家中几口人,做的什么营生。 如今名字是假的,身份是假的。 我不死心,让阿姐问问江湖中的朋友,是否听说过萧恒这个人,每次得来的都是摇头。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,渐渐的也不想去寻希望了。 洛阳王城的春节,比之在陶然山时候的冬天,要热闹不少。 家家户户灯火通明,鞭炮声昼夜不停。 父皇赐了我好些膳食,很是可口。想吃上一些,但又懒得动,阿姐便一口一口地喂我。 仿佛又回到了小时那般娇气的日子。 又过了半月,在万家团圆夜之际,我临盆了。 娘胎带出来的不足,费了我好大力气生出,差点一尸两命。 但孩子却很健康。 是个男孩,他出生在元宵,小名便叫元宵。大名叫商祁弘,冠以天驰国姓,是他的国君外公取的。 及至立夏,我才养好身体。舅舅对我的膳食十分看中,每日都要定时定量。 不知是福是祸,因着这次产后修养,身体倒比调养了十八年的还要康健几分。 五月十八,天驰国颁布旨意,迎长乐公主回宫,大赦天下。 次日,一辆马车驶出了洛阳城。 马车中的人,是我和阿姐。 “我已与父皇相商,想去母亲游历的江湖看看。” “祁弘拜托给了舅舅与舅母,他们亦同意了我去外面走走。” 乖巧了十七年,这两年来,全是反骨。 阿姐摸了摸我的手,无声地安慰我。 “五月谭城,海棠花开,我们就去阿姐的故土看看吧。” 我打开车帘,吩咐杞临,“往南,去谭城。” 杞临,是父皇予我的贴身侍卫,武功高强,已达应龙的境界。 “是。” 驾马前行,前程几何,莫忘归程。 8路途遥远,路上走走停停,于各处小镇歇息。 行至一处地方,名唤巧溪镇,比之他处落魄不少,一路有不少饥饿瘦削之人。 我们于落日茶楼停歇,茶楼处鱼龙混杂,各种声音不停。 “我听说,江湖甲字悬赏令被莫阁的人揭下。” “是谁?” “不知道。但无论是谁,都会引起腥风血雨。” “没错。不过,悬赏令上写的是什么任务?” “据说刚一发出,就被莫阁的人就揭下,没几个人看到。” 又有几个人加入了讨论。 “我听说,是江湖第一美人发出的,要杀了江献那厮。” “不,我听说的是水云派的人要杀了道君与柳月娘。” “我这个才是最可靠的,是要杀了一个朝廷命官!” “戚。” “去去去。” 一帮人为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事,竟然差点打起来。 我笑着摇摇头,收回了对他们的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shenjincaoa.com/sjchq/1216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山清水秀的上山百草园,传承中医中药,草药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